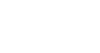不知道现在高考复读的人多不多,我们那个年代,高考复读的人特别多。不复读三五年,家里很难出个大学生。而在我的同学中,有人复读八年才考上,胡须比头发还长,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,他的执着。
我是1995年秋季入读“朝大”复读班。我们之所以称“朝大”,而不叫隆回县朝阳高考补习学校,是因为来这里参加复读的人,等于有一条腿已经跨入了大学的门,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预科班。叫的人多了,我们潜意识里就只知道“朝大”,反而忘记了学校的真名。
我入读时高考分数比较高,老师特意安排在中间位置坐,而高考分数比较低的同学便安排在两旁或靠后。一个班有一百多个同学湖师大二附中复读一学期,前靠着黑板,后挨着墙,中间过道很窄,侧着身子才能通过。

也许是“两耳不闻窗外事湖师大二附中复读一学期,一心只读圣贤书”。我们同学之间交流极少,如果不是通过其他同学介绍,真正能让自己叫出姓名的同学,绝对不超过三个。那时复读压力大,一心想考大学,除了吃饭就是读书,叫不出同学的姓名也不奇怪。

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位同学是小沙江的,真名真姓忘了,知道他的外号叫胡子多。他也复读好几年了,很多知识点比老师掌握牢固。他经常用背对着讲台,跟我说老师水平不行,误人子弟,书不是那样教的。只是高考前一个月,他不见了,很多人说他闭门苦读,当年好像考上南京政治学院。待我走向社会,感觉这个人不简单,如果能修炼自己的品性,或许会有一番作为。直至现在,我一直打听他的下落。无奈,不知真名真姓,寻找起来很渺茫。

在班上,我喜欢一个女同学,长得高挑,满脸红润,文章写得好,有点像《红楼梦》中的林黛玉,走路宛如一阵风。胡子多怂恿我给她写情书。我写好后,利用晚上自习时间,他真帮我送过去,对那女同学说有人喜欢你,弄得其他同学哈哈大笑。大概过了三天,女同学私下找我,说到外面一起谈谈。我红着脸,像个犯错的小孩,跟她出去了,那是一片坟地,石碑林立,阴森恐怖,有些吓人。她塞给我一张纸条,再三叮嘱我回宿舍才看。我很老实,真回到宿舍才打开纸条。上面写了三个字:“神经病!”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样经历这个打击的,只是后遗症真落下了。我不敢再追女同学,怕别人说我是神经病。甚至觉得没有考上大学,没有事业,恋爱是很可耻的事。直到28岁,我才鼓起勇气追女孩,就是我现在的妻子。

昨晚去石龙古镇,曾俊跟大伙介绍,说我是他的同学湖师大二附中复读一学期,我当时疑惑许久,甚至纳闷我们怎么是同学呢?应该是讲错了吧,我们是同乡,一起喝辰河的水、吹雪峰山的风长大。后来,他跟我讲,1995年秋,他也在“朝大”复读,并说哪位同学考上复旦大学,哪位同学考上吉林大学,哪位同学考上中央财经大学,哪位同学考上湖南师范大学,他大学毕业后考公务员来了东莞……一一比对,发现我俩真是同班同学。只是那时,他不认识我,我不认识他。到了东莞,很多人经常提到我,甚至在江湖有很多关于我的传说,他打听,才知道我俩在一个班复读,是货真价实的同学。

还有一位同学叫刘权,考上北京邮电学院,以前在北京市邮政局工作,后来下海经商。我在北京设立办事处,找他租办公室。相见相识六年,他叫我罗总,我叫他刘总。如果不是上月去北京参加会议,不与他在办公室聊复读往事,真不知道我俩当年在“朝大”也是一个班的同学。他属于比较顽皮的那种,读书时竟然把大哥大拿来了,让全班同学好生羡慕。因为是同学,因为彼此熟悉,见面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讲礼节,直呼其名:“刘权,我要投标,你去给我拿下标书。”他也笑呵呵地说:“罗建云,遵命!”末了会讲一句:“如果中标了,给跑腿费不?”我说:“老同学了,就给个锤子,给个毛线……”
也是昨晚,知道有同学后来考上北京大学博士,有同学成了大学教授,也有同学主政一方。而我,没能如愿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,反而被中国社会大学农民系录取。1998年南下,从泥水工开始,做过普通工人,做过品质管理员,在外资企业做到部门经理。如今,为了一日三餐,在南方的天空下努力奔波……
(作者系民进会员、东莞市作家协会理事,出版有散文集《人生四十年》。本文略有删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