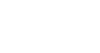考上大学对我最大的改变可能就在于此,我走出了山西省,去外省看了更广阔的世界,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,而在每一个尝试的过程中,都能看到自己人生的画卷在徐徐展开,在大学的那一切就像在冥冥之中,把我引向了现在的人生。
大学毕业时,穿着学士服的“我们”。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 摄
文丨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
编辑丨陈晓舒
校对丨刘越
►本文4816字 阅读9分钟
“高考”是许多人的共同回忆,曾经在操场举着单词本背诵,也曾为了某个科目彻夜苦读。那时的我们,为了梦想而拼命向前。那时候的回忆也在时间的打磨下格外珍贵。
六月是专属于高考的月份,充满了青春、汗水、眼泪、笑容的味道。在高考前夕,八位不同年龄的人向我们回忆了高考往事。
他们中有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,有考了26次仍要参加高考的“钉子户”,有从大山中走出来的女孩。他们的故事横跨了大半个世纪,带着时代烙印和厚重的书本气。
再回看,轻舟已过万重山。

走出去
谭女士 27岁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 西南大学 2014年高考
我是95后,同时也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。对于我们这一代中的大部分人来说,读高中考大学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生选择。但对于我小时候的朋友来说,这个事情是不在人生规划里的。我的11个小学同学里,其实只有我坚持读到了高中。
我的爸爸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村庄。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里,他非常守旧,不愿意接受更多科技产物,甚至到现在我们家还是用牛去犁地。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,就告诉自己,一定要走出大山,走出这里去看看世界。
其实我对大学的理解,可能非常功利,它只是我走出大山,获得一个工作的途径。只是这个途径是我当时唯一的路。
谭女士的家乡。受访者供图
贾先生 38岁 山西大同人 武汉科技学院(现武汉纺织大学) 2003年参加高考
我是2003年参加高考的,那一年也很特殊,从年初开始,全国遭遇了“非典”,在高考之前很多学校都停课了。不仅如此,从2003年开始,高考的时间也正式从7月改到了每年的6月7日。我几乎是在一片迷茫与焦虑中参加了高考,走向了成年。而我对高考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年的数学题特别难,我是我们文科班唯一一个数学考到及格线的。
那时候查成绩还要不停地打电话,我打了三通电话才不占线查到了成绩。
我爸爸把“上大学”看作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,因此在开学前,给我在大同买了一套西装。开学时我穿着那套西装在学校食堂吃饭,学校食堂的工作人员路过我都要说“师傅,麻烦让一下”。我的同学们哄堂大笑,我才意识到我和父亲都有点“老派”了,现在的大学是年轻而自由的。
在那四年里我的朋友们都在参加各种社团活动。那时候音乐是最流行的爱好,男生为了追女孩,都流行去学点音乐,学点吉他。大四毕业那一年,我们甚至办了一场告别的音乐会,我为此还自学了架子鼓。

考上大学对我最大的改变可能就在于此,我走出了山西省,去外省看了更广阔的世界,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,而在每一个尝试的过程中,都能看到自己人生的画卷在徐徐展开,在大学的那一切就像在冥冥之中,把我引向了现在的人生。
贾先生年轻时的照片。受访者供图
郭女士 24岁 河北沧州人 北京某211大学 2017年高考
我其实参加了两次高考,第一次成绩我很不满意,几乎是在一片不理解的声音中选择了复读。
我爸爸觉得没面子,不同意我复读,甚至断了我的生活费。同龄的同学里,要么随便读了一个普通的学校,要么高中毕业就立刻出去打工赚钱。那时候他们提到我甚至会说,怎么这么不孝顺,不知道早一点出去打工赚钱。只有妈妈相信我支持我,让我抛下一切,遵循自己内心的选择再读一年。沧州没有专门的复读学校,好在我的高中班主任要再带一年高三,我可以跟着她再学一年,但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完全无法融入的班级。
很多同学都会戏谑地称呼我为“学姐”。我记得特别清楚,每当老师提问,同学回答不上来时,他们就会说:“老师你问学姐吧,她都读过一年了,她肯定什么都知道”。我在班里没有朋友,每天陪着我的只有学习和做题。那时候我最期待的事就是考试,因为每一次当我看到成绩单和贴在外面的优秀学生名单时,我就可以不断地跟我自己说:“你做的一切都不是白费的湖南师大二附中复读部高考成绩,你吃的苦都不是白费的”。我知道这很病态,但就是这样的心态支撑我走过复读的那一年。
之后我来到了北京读书,大学那四年几乎治愈了我,再也没有人关心我为什么复读了,也没有人埋怨我为什么不早一点赚钱。爸爸也开始逢人便说,我是他的骄傲。我成了我们家那一片有名的大学生。
或许是因为我成为了一个“有本事”的小辈,家里的长辈也不再管我,只是偶尔我回到沧州,他们会问我,都24岁了,什么时候结婚啊?我笑笑没有回答,然后想起,真奇怪啊,在北京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。
在北京的这几年,我认识了一个女老师,50岁了,没有结婚,独立又充实,我看到她觉得这样的生活也好令人向往。而这样的生活在我家,我想大概会被除了妈妈之外的每一个人反对吧。
郭女士在北京阜成门桥。受访者供图

为了他
马锦欣 33岁 河北衡水人 河北经贸大学 2008年参加高考
2008年我读高三,那一年冬天华中和华南地区遭遇雪灾,田里很多农作物都受了灾,后来临近高考又发生了“汶川地震”,现在回看,我们那一届学生在各种各样的大事记中迎来了高考。
考完的那一天,爸爸从农村来县城的学校接我回家,因为到了北方的农收季节,沿途大街上都是家家户户晒的麦子。爸爸问我:“考得怎么样?”那天我就在麦子味的风里和他讲考题。这是我们俩从小的默契,因为爸爸有一个理论,那就是如果你能回忆起考试的题目那就说明你考得还不错。
后来成绩出来,我打完第一通询问成绩的电话时,有点蒙,成绩好得出乎意料,于是又花一块钱打了一通电话确认,是645分。
说实在的,这是很高的成绩,但那时候我们家里没有大学生,也不懂怎么选择学校,最后我选择了河北经贸大学。上大学的第一天,我对大学还没有任何的概念湖南师大二附中复读部高考成绩,出了火车站居然看到大学有校车来接新生,那一刻我突然有了归属感。
而在大学里有一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,我参加了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,报名了贵州省的项目。做这个决定是因为我14岁时了解到2004年的“感动中国”十大人物中徐本禹的故事。我看到徐本禹放弃读研的机会选择去贵州支教,被深深地感动了,我也想像他一样去帮助一些人。于是我填了当时西部计划里最艰难的地区之一——贵州。
当时西部计划的最长期限是三年,三年志愿服务期满之后,我本来是要回老家的,但正好遇到贵阳的事业单位考试。就这样我留在了贵阳,一直到现在。对我来讲,如果我没有读过大学,那我就没办法去贵州,没有办法去亲身体会自己小时候非常崇拜的人做过的事。
马锦欣大学时,去福利院参与志愿者工作。受访者供图
小孙 18岁 即将参加 2023年高考
我为什么要上大学:浅显地说,为了面子。这其实是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个原因。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一直都很爱我,但是从小升初到中考我都没有很认真地学习,一直都让他们失望。在我都渐渐接受自己平庸的现实时,他们却一直视我为最大的骄傲。

记得有一次下校车是爸爸来接我,他跟我说他从《读库》开始办的第一版就订了,订了十几年了,说自己品位很不错。夸着自己潇洒往事和高端品位突然掺杂一句:“爸爸多厉害,你看我女儿,你看看我女儿!”我当时就很想哭,长发的愤青少年转眼成了我中年秃顶的父亲,他一生中无数狂妄酷炫的时刻最后到头来最让他骄傲的却是我。
我经常庆幸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教会我不拐弯抹角地直接说爱。这就是我要考大学的最直接的原因,为了让父母相信自己的女儿能照顾好自己,有能力,能让他们真正感到骄傲。
小孙在为高考做最后的冲刺。受访者供图
别给人生留遗憾
梁实 56岁 四川人 高考“钉子户” 即将参加第27次高考
马上过几天,我就要参加我的第27次高考了。1983年的时候我16岁,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高考,但准确地说我参加的并不是高考,而是高考前两个月的预试。但大概是因为自己不努力,预试就被刷了下来,我的第一次高考经历就这样草草结束了。后来几年我又考过几次,直到1987年才第一次通过了预试,参加了一次真正的“高考”。
大概从那时候起,“我要上大学”的念头就在心里扎了根,那时候就想着,考上大学,我就可以成为教授,成为工程师,总之就有机会成为那些别人一提就肃然起敬的人吧。然而一直到20多岁了,我还是没有考出来,于是只好开始工作,之后又结婚生了孩子。
2001年高考报名政策调整,取消了年龄限制,允许25岁以上的考生报名参加高考,于是从2002年开始,我只要不忙都会报名参加考试,过几天就要参加我的第27次高考了。关于这次高考,我的目标是达到重本线。如果考上了,我是肯定要去上学的,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会和年轻的娃娃们相处不好,因为我心里清楚,我虽然50多了,心理年龄也还是十几岁。
考了这么多年湖南师大二附中复读部高考成绩,很多人不理解,“你就算考出来了都好多岁了,怕还是没得单位要你”。这么多年我听见这些话也不回复了,我想他们总是不懂我,我就觉得除了现实的东西以外,人还多多少少有点精神追求吧,我一想到自己没上过大学就心情挺不愉快的,我想要自己快乐,这是我大学梦。
我的人生里其实放弃过很多事,但就是高考,可能20多年里偶尔有过“算喽”的念头,但到了第二天我又会跟自己说,不行,我还是要考,不然一辈子没上过大学,我始终是遗憾。

梁实在为今年的高考做准备。受访者供图
小刘 25岁 湖南人 武汉大学 2015年高考
如果回到八年前,让一个“小镇做题家”去想象大学生活,恐怕想象的空间都很有限,好比让一个一直生长在内陆的人去想象海滨生活。我想那时我最期待的,应该就是如果我选择中文系,就再也不需要学数学了。
这几年和朋友聊到高中生活总是齐声感慨,高考可能已经是我们这辈子能承受的压力的极限。想起高考,想起我在那所以衡水中学为模仿对象的学校里度过的三年,想起被理所当然取消的体育课,想起常常发脾气令全班害怕的数学老师,想起在南方潮湿的没有淋浴系统的宿舍里打水洗澡,想起总是飞奔着去食堂、去教室。
但好在我的人生确实被大学生活重构了,但我拒绝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去列举我从大学获得了什么,这样的列举令我不安,因为在“小镇”中成为“做题家”并顺利接受“高等教育”、从而拥有走出“小镇”的选择权,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,还有很多人因为家庭、经济等原因连做题家也没得做。
对于小镇人来说,受限于资源、信息,一些简单的道理和法则我们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参悟,那就祝福我们吧——祝我们都能拥有在各种各样的“标准”“范式”之外看到更多可能性的勇气,不畏惧面对最真实的自己,去拥抱所谓的“边缘”与“少数”,向更自由、更开阔走去。
小刘在校园里借用路灯的投影模仿小狗。受访者供图
徐树海 64岁 河北人 铁道部大同机车厂技术学校 1977年参加高考
我是1959年生人,从河北农村高中毕业的时候是1976年,高中毕业之后就立刻跟着要下乡的父亲去了河南农村。1977年10月,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,决定要恢复高考。我就在河南当地报了名,而那一年的高考是在冬天。后来考试成绩出来,我没有考上,只好再回到河南的农业生产队里工作,干一天活是七个工分,十个工分可以赚1角3分钱。但如果能去工厂的话,工资就能高一点,也能轻松一些。那时候除了农业生产队之外的工作,基本都要考试,想要进厂工作也有每个厂的考试。而如果参加了高考,考上了学校是有机会分配到国企工作的,于是我决定要继续高考。
为了高考,我就白天在生产队上工,晚上复习。直到1979年,我考上了铁道部大同机车厂技术学校。这是一所技校,用现在的话说,这根本算不得什么大学,但是这个学校管分配,读完就能进铁道部工作,还不用交每个月18元的学徒费,这在当时已经是顶好的工作了。
回想起来,那时候想上学其实也没什么别的想法,就是想多赚点钱,多走点路,多看看人吧,总不要一辈子一天只赚七个工分。